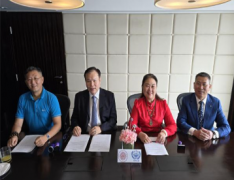- 临沂市曲艺家协会郯城分会在高峰头 山东聊城市文化和旅游行业党委召开
- 众识网甘肃站于2024年2月3日正式成 山东聊城市直书画家协会开展“迎新
- 2023两河之约(聊城)书画艺术展书 白河林区基层法院政治部新年寄语
- 山东沂南:孙祖小学开展春节文明实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坚守岗
- 白河林区基层法院:新年贺词 茶宝宝公益摄影活动全国征稿启事
- 临沂市曲艺家协会郯城分会在高峰头 山东聊城市文化和旅游行业党委召开
- 众识网甘肃站于2024年2月3日正式成 山东聊城市直书画家协会开展“迎新
- 2023两河之约(聊城)书画艺术展书 白河林区基层法院政治部新年寄语
- 山东沂南:孙祖小学开展春节文明实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坚守岗
- 白河林区基层法院:新年贺词 茶宝宝公益摄影活动全国征稿启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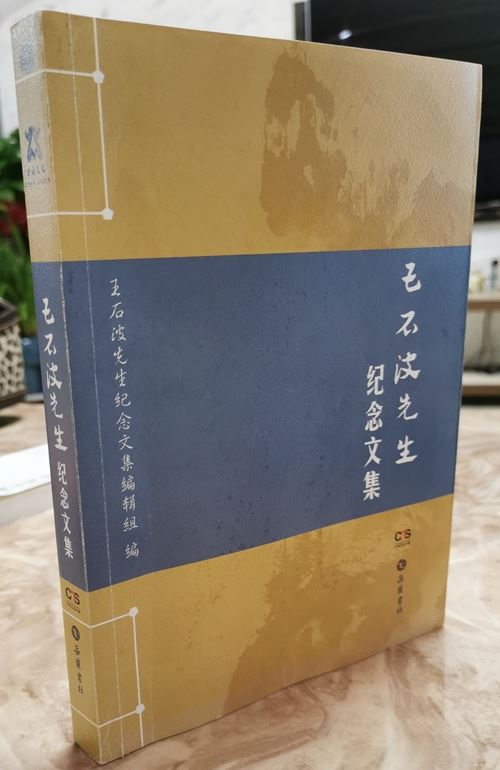
前不久,吾友刘良洪仁兄赐我珍宝——一册由刘善泽先生少子刘永孚牵头保存整理出版的《三礼注汉制疏证》。从前学习了解先秦政治制度时翻过最为权威的“三礼”之首、郑玄注的《礼记》。刘善泽先生写这部著作就因为“尝病郑注《三礼》所引汉制宿滞沉疑”,于是下功夫“甄采群集,转相发明。析音义,审名实,补缺略,正违失”。我们在湖南师院读书时中文系的台柱子之一王石波教授是刘善泽弟子,石波教授为《三礼注汉制疏证》写有跋文,称其老师著作“取证闳博,比考缜密,一名一物,必求其征。诚治古籍及故训者之师资”,是有益于中国学术的一部大书。王石波先生女儿王小璜是我们大学同学,前年来浏阳时,我忘记了问她“令尊是刘善泽先生的得意门生,我们那时候怎么只晓得石波先生是著名的外国文学教授呢”?那个时代教授的学问底子真是不能不让人折服啊。(2821年4月18日《湖外诗人第一刘》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读高中准备参加停了十年刚刚恢复不久的高考时,政治课中有个极重要的知识点便是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第四次路线斗争错误的一方就是罗章龙的分裂主义路线。罗章龙这个负面符号由此刻进了我心里。只是那时还不晓得这个分裂路线的“坏头头”是我们浏阳人。上了大学,那时候有一门公共课叫做现代革命史(实际上就是一九四九年中共党史)。记得上课的是一位女教授,很负责,上课很有激情。那个时候我们的大学教育还是以传授特定的知识(特定的知识有些是错误的,比如把账全算在个人头上的所谓路线斗争的提法后来就被抛弃了)为目标,而不是着力培育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但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已经开始学会独立思考了。对着讲义听完女教授讲在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那一节,我就犯糊涂了。(2022年10月18日《冥冥之中的说不清道不明》
我从学校改行后,第一个工作岗位是政府经济研究室主任。实际就是做文秘工作,主要的任务是调查研究、起草重要文稿。为了做好工作,我经常向茂荣和卧云两位老同学请教。茂荣是高中同学。卧云是大学同学。他们一位在省会长沙,一位在四川成都。很巧的是,没有任何交集的他们几乎在同一时段强烈建议我读点西方哲学。我自认为是阅读爱好者。他们俩的建议对我而言却真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茂荣和卧云都安慰我没基础并无妨碍,关键是要点毅力。茂荣说可以从容易懂的一家读起,比如马克思·韦伯,再往上溯。卧云要我先了解一下西方哲学史,再下点蛮力从康德的三大批判钻进去。两位同学都知道我从前读书完全是凭兴趣读点耍书,他们都担心我将他们的强烈建议置若罔闻,于是先后从成都、长沙给我寄来了黑格尔的四卷本的《哲学史讲演录》和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电话里还说到时要跟我讨论一些问题。这自然是逼鸭子上架的搞法。我不知道在两位老同学的指引下,死啃了好长一段时间的西方哲学后,对当时自己做好本职工作是否起过些许积极作用。但仔细想想,从一个新的视角明白了现代社会的来路,从而懂得坚守价值底线,坚持独立思考,对人对事对理论不盲从迷信,这对于我能以一种比较认真的工作状态和相对洒脱的生活姿态在行政上安然“混”过将近三十年时光应该是构成了一个比较牢靠的心智支持系统。我甚至可以确信无疑,这次被两位同学逼出来的跨界阅读对于我的人生具有点亮了一盏心灯开启一个精神世界的意义。(作者:吴震 编辑:汤伟 责编:韩同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