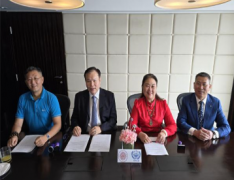- 临沂市曲艺家协会郯城分会在高峰头 山东聊城市文化和旅游行业党委召开
- 众识网甘肃站于2024年2月3日正式成 山东聊城市直书画家协会开展“迎新
- 2023两河之约(聊城)书画艺术展书 白河林区基层法院政治部新年寄语
- 山东沂南:孙祖小学开展春节文明实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坚守岗
- 白河林区基层法院:新年贺词 茶宝宝公益摄影活动全国征稿启事
- 临沂市曲艺家协会郯城分会在高峰头 山东聊城市文化和旅游行业党委召开
- 众识网甘肃站于2024年2月3日正式成 山东聊城市直书画家协会开展“迎新
- 2023两河之约(聊城)书画艺术展书 白河林区基层法院政治部新年寄语
- 山东沂南:孙祖小学开展春节文明实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坚守岗
- 白河林区基层法院:新年贺词 茶宝宝公益摄影活动全国征稿启事



关于徐渭书法的评论很多,有的令人信服,有的令人半信半疑,有的令人难以苟同。本文拈出其中较重要的三条,说说自己的看法。
其一:“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据说这是徐渭的自评。我以为,自评其实并不一定可靠。自评往往带有个人的偏见,或者另有意图。如同齐白石自评说“诗第一”,“画最次之”。一些人就觉得老人似有“欲擒故纵”之嫌。徐渭生于1521年,诞辰于今已五百周年,这五百年的历史对徐渭的综合评价是画第一,诗文次之,书法居其末。徐渭的书法在当时的明代甚至上不了台面。历史现实与徐渭自评正好相反。明代是中国书法的成熟期,台阁体的出现,就是成熟的表征。明代书法,对我国整个书法史而言,决不能小觑。明初有三宋二沈,即宋克、宋璲、宋广、沈度、沈粲。沈度乃台阁体之祖,被明成祖称为“我朝王羲之”。明中期则有李东阳、吴宽、沈周、王宠,还有大名卓著的祝允明、文徵明。晚明则有邢侗、张瑞图、董其昌、米万钟、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明代书法衮衮诸公,是一座座书法高峰。单就书法论,徐渭在这些高峰面前,没有位置。我读张光宾先生的《中华书法史》,其中明代一节,只字不提徐渭。但,历史也可以改写。在当下特定的“现代书法家”的提携下,徐渭的书法正在重新评论,重新发现。现在的中国书法史徐渭的地位在明显上升。徐渭的书法,主要是草书。他的草书有很明显的个人内心情感的宣泄,笔墨恣肆,满纸狼藉,不计工拙,所有的才情、悲愤、苦闷郁结都隐含在扭曲的笔画之中了。他的书法,有强烈的个性,明显与有明三百年正大气象的主流书法拉开了距离。徐渭说:“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者非高书。然此言亦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这句话,与其说他“自负”,不如说他“失落”。徐渭是一个多才多艺、出类拔萃的人,时代的扭曲使他从天才演变成怪才。从他的书法看,他有很好的笔法技能,从他的书论看,有很高的见解,但他留下的书迹,最大的缺点是行笔失控,章法无序,狂放不羁。可以看出,徐渭不愿受法度的约束。但,法者,约束也。书法、法书,本不该离开法度的限制和约束。也有人以为,从徐渭的自评来看,说明他是个明白人。他把成就最低的书法,说成是“第一”,成就最高的绘画,他却说是最次。从这里,我们看出了他的狡黠。也就是说,徐渭的“吾书第一”,正说明徐渭对自己书法的不自信。他的自评,应该符合徐渭的性格特征。这一说法,可供讨论。
其二:“文长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余不能书,而谬谓文长书决当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徐渭死后20年,“公安派”领袖人物袁宏道到绍兴探望友人陶望龄,晚间少睡意,无意中翻到一本徐渭的诗文稿,读了几篇,不禁拍案叫绝,惊问此人是今人?还是古人?竟拉起陶望龄一起彻夜阅之,“读复叫,叫复读”,以致把童仆惊醒。而后袁宏道不遗余力地搜罗徐渭的文稿,研究徐渭,大力宣扬徐渭。袁宏道还写下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小传《徐文长传》。《徐文长传》主要评的是徐渭的诗文,偶及书法;评徐渭的书法就是上面这一段评语。对我来说,拜读这段评语,使我惊叹的不是徐渭的书法,而是袁宏道令人震惊的文笔。袁宏道坦承自己“不能书”,他谦虚地自称他的书评只能是“谬谓”(直译为“错误地认为”),但他涉笔一点,就把徐渭的书法提高到明代大书法家王宠、文徵明之上。袁宏道知道有人会提出异议,他却已声明在先:他论的是“书神”,不是“书法”。提到“书神”的高度,这官司就没法打了。接下去他又说徐渭是“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更是令人摸不着头脑。何谓“散圣”?何谓“侠客”?几品几级?标准何在?只有请我们这些“后之览者”各自发挥想象了。我的理解,袁宏道的“散圣侠客”其实是指出了徐渭书法的“另类”,但他是以肯定、赞美的口吻指出的。经袁宏道这样一说,令多少人在不可捉摸的“散圣”、“侠客”前佩服得五体投地!整段评语唯一能落实的是“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但这一句评论,评的其实是徐渭的诗。袁宏道是性情中人,激情满怀。他以他的慧眼和文笔,写下了著名的《徐文长传》,使徐渭死后复生,确立了徐渭的历史地位,造就了徐渭500年的辉煌。如果没有袁宏道,也许我国历史会遗忘了这位影响独特的大画家。徐渭抑郁一生,有袁宏道这篇《徐文长传》,可以瞑目矣。但其中袁宏道的这段书法评论,实在是写得肆意汪洋,不着边际,明显有爱屋及乌之感。借用米芾的话来说,应该是属于“征引迂远,比况奇巧”之类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