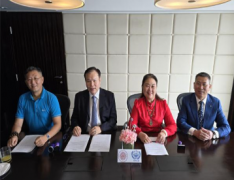(沙 柳)
当远在西京的李二牛,接到黄塬打来的电话时,嘴巴张得很大,眼睛也略有些突出,但是他始终没有发出任何声音,面对耳边传来老村长的声音,他不知道如何挂了电话,他的大脑短暂停留了五六秒后,又瞬间高速运转。
他首先想到的是瞎眼老娘,此时,正坐在后炕上,手里捏着一根沙柳棍棍,随着哭喊声,颤颤巍巍,满头白发有些凌乱,哦!凌乱是不能形容出来的,就拿黄塬的一种植物来形容更恰当不过了—沙蓬。他能想象出周围坐满了邻家的婆姨婶娘,正七嘴八舌地安慰着老人。老人睁着两个空洞的眼睛,好像搜寻着什么,手里捏着的沙柳棍棍,轻微地抖动着,最后,哭喊声变为一声声呻吟。
随后他又想到年幼的妹妹,一个人依靠在门框上,不知道窑洞里发生了什么,慌乱无助的眼神令人怜悯,此刻,她心里会想些什么哪?首先想到的是她二哥吧,他应该放学还没有回来。哎,回来了,又如何给妹妹答复大人们的悲痛。又暗自庆幸,好在有弟弟照看妹妹,省的给这场灾难添乱。二牛比他们两人大十多岁,初中没毕业就外出打工,一年四季漂泊在西京城,这二年在工厂做工,也算有了固定做活,所以家里有什么事,都会直接打到工厂门卫处传达室,平时二牛舍不得休班,多挣一点是一点,农村娃娃嘛,在这西京城没什么朋友,更何况亲戚熟人。只有过年才回家与家人短暂的团圆。所以弟妹两人和大哥有些生疏,二牛每次回来,都会给年幼的弟弟妹妹买些学习用品和好的吃食。
紧接着他又想到,只有十二岁的弟弟,脸上还挂着天真无邪,却俨然一副小大人的架势。回到家中,放下书包,默默地拉着妹妹的小手,去后山打猪草。因一年四季,他和父亲奔走在外面做活,家里有些零碎的营生,只能落在这个小大人身上。当然,这个孩子会意识到什么,大人们看到放学回家的三牛,说话声音有些低声唤气,这个年幼的娃娃,只能用黑豆般的眼睛猜测,谁也不会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村长,气喘吁吁地走上土坡,进了李二牛家的院子,刚巧与三牛在院门口碰上,三牛抬头看到这位本家叔叔,叫声二叔,是不是我大捎回来什么了,还是我哥?眼下村长有些难为情,要是以前的话,村长会逗一下这个懂事的娃娃。此刻,村长只好轻描淡写地说,你哥过几天回来,他特意让我来通传一声,匆忙走进院子。
窑洞里的邻家婆姨婶娘们,听见院子里村长和三牛的对话,顿时大家心里都踏实多了,透过玻璃窗子都向院子里张望,同时对着二牛的娘说,村长来了,毕竟村长是这个村子的主心骨。村长站在院子中央,望向院子外,三牛牵着妹妹小花,正向对面的小山坡走去。哎,村长叹了一口气,挑起窑门上的粗布帘子,侧着身子进去。
且说,村长李林才,毕竟是见多识广的人,早年间在某部队服役,从前线枪林弹雨中活下来的人,一次战役中,只因掩护身边的战友,被敌人的一枚炮弹落在身体附近,当时,整个人血肉模糊,后经多方面救治,身体虽然康复,但是体内留下十八块弹片。尔后,复员归来,主动要求回村务农为主,不为国家添加任何负担。
回村后,这不,由于本村子土地贫瘠,多为沙石洼地,劳作一年,反而难以养家糊口,这些事,自然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找老村长商量。老村长自是有心无力,看到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不由得暗自感叹,想想自己一辈子和黄土地打交道,恪守本分,尽不敢有这种胆大的想法,一开始惊得合不拢嘴巴,仔细端详眼前这个年轻后辈,当年鼻塌憨水的碎娃,没成想去部队锻炼了几年,眼界竟如此开阔,老汉不由得感慨,自家二小子,当年让去当兵,死活不去,唉,娃他妈惯坏了。要不然他这个支书也有了继承人了嘛,更要命的是人家在部队上立了几次功,又在是部队上入了党,这放眼黄塬上也没有一个人能比嘛。老汉续想自家娃娃虽说没有去部队锻炼,跟他国营单位的姐夫干采购,这几年也算是转正,成了一名吃皇粮的。
当下,老支书也好考验下这个本家碎娃,看这几年长了多少本事,有没有能力挑起这个大梁。主意打定,不动神色,由这位本家碎娃折腾,自己则帮忙吆喝,暗中跑前忙后,害怕这些二杆子后生,做出格的事情,谁承想,近一个月的工程进展,他干得游刃有余,现在看来,老支书的担心多余了。尽管如此,这个贫瘠的村子,绝不能再出一丁点事。
在老支书的号召下,李林才组织了本村的青壮年,声势浩大地打井修坝,在村中人员集中土岗上,硬是打出两眼出水很旺的甜水井,先后扩展五十多亩旱地,三十亩水地,外地引进了桃树、梨树、苹果树、葡萄、枣树等水果树,彻底改变了对碾子村的面貌,改变了别人对黄塬乡甚至古木县的看法。这些我后面再说,打井见水的做法,可以说在碾子村还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老先人几辈子都是打旱窖,靠天吃水,虽说从未放弃打井的念想,然而,碾子村平凹的地方早已千疮百孔,就是不见有半点水。有些井深达到人力的极限,光挖井每十年死伤七八人,再到后来,人们也就认了命,不在打井,坐等靠天吃水。
老汉想用不了数十年的光景,不、不,也就三四年的光景,完全能告别靠天吃饭,更有能力摘掉青黄不接时,全村老弱拖拉着去黄塬沿街乞讨的局面。
贫瘠的碾子村,在老支书的帮扶和李林才带领下,终于丢掉手里的讨吃棍,周大方圆的女子都抢着往碾子村嫁。黄塬和县上给老支书和李林才戴了几次大红花,组织周边的村镇向碾子村学习致富经验。老支书是最好的活宣传,隔三岔五被邀请的做报告;而这期间,老支书也卸任了,把这两百来号人的担子交给了李林才。
在李林才的带领下,就地取材办砖窑,烧制出来的砖,销售在黄塬周边的城镇及村子,慢慢地将原先的土窑、土坯柳把俺房子,逐渐更换成亮堂的青砖木头橼红瓦房。自行车、轻骑摩托、小型机械手扶拖拉机,成了碾子村的标配。更有年轻人,向往大山外面的天地,三五结伴闯荡,这不,本村的李二牛就和几个玩伴结伴,去了西京。
二
“轰”的一声,空顶部分岩石瞬间脱落了下来,正好落在李林林的身边,众人愣愣地僵在那里……
煤都发生的一起顶板空顶事故,而我们的主人公李林林也在这次事故中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当矿主将电话打到村委会时,也就有了我们开头看到一幕。
且说,李林林是李林才本家兄弟,在李林才回村带领众人大搞基建时,李林林通过婆姨的姑舅另谋出路。经婆姨姑舅介绍,在煤都冕盖仡佬私人煤矿成为一名掘进支护工。工资收入相当客观,这不,经过五六年打拼,自家盖起了清一色五间砖瓦房,在碾子村也是迈进了小康家庭。长时间在掘进工作劳作,身体也捞下疾病,一到了冬天就不好呼吸,李林林也只能辞职,回家务农。
好日才开始,李林林婆姨突然得了眼疾,一开始是眼里一片灰蒙,后来慢慢地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周大方圆的医院看遍了,也不见好转,家里的一点积蓄,眼看就花完了,老汉和婆姨商量,找找关系,咬咬牙,在下几年井,两个娃娃还在上学,以后花钱的地方多了,大小子虽说初中没毕业,好在勤奋好学,现在也在西京找了一门学手艺的活,将来也是可以养活自己的。
李林林来到曾经的煤矿,经婆姨的姑舅介绍,分配到掘进队,简单的培训完后,就同掘进工人下井作业,当然,干的还是老本行,掘进支护工。
随着掘进工作面的延伸,巷道支护缓慢,刚好煤炭市场进入黄金时候,从上到下追求产量,忽视了安全,煤层上面的顶板岩层失去了支撑,原来的压力平衡遭到破坏,煤层顶板在上覆岩层压力的作用下,发生变形、破坏。管理体制混乱,冕盖仡佬私人煤矿属集体与人个联办五股矿,建立有董事会。实行承包后有承包人,承包人又雇用矿长,雇用矿长而又不是企业的法人代表。这样一个复杂的机构,却责权利不统一,给企业的管理造成混乱。在这样的环境下,发生了本次矿难,一人死亡,三人不同程度受伤,李林林当场死亡,矿方赶紧组织人员一来报丧,二来全盘人不离身,商洽善后。
最后,矿方私下处理了这起事故,给受害人赔了些钱,这事算是压了下去。
这刻,李二牛跪在碾子村西山上,李林林的坟疙堆前,泪眼婆娑望向自家院落。过往的事,历历在目,老实巴交的父亲,操劳一生,与大地长眠。深秋季节,西北风在山峁上哀嚎,一股股瘦风刮起稀稀拉拉的落叶。
李二牛站起身来,用袖子擦掉眼泪,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夕阳下的家。
无题
昨日的风
再也刮不起曾经的岁月
夜晚静悄悄
是多么熟悉的旋律
这一生啊,
将我的灵魂定格在夜晚
忧郁的眼神
读不懂白玫瑰里的暗香
也许,
心中念念不忘的记忆
才是真真的快乐
在夜晚里温柔了整片天空
闪烁的流星划过天际
所有的秘密只能吊挂在夜晚里
时光不轻,流年逝水
一声“再见”,一别两宽
抓不住的温柔
留不住的风
……
作者简介:
沙柳,原名:王利雄,字:觉也,号:疯癫散人,男,1985年出生于陕西神木,榆林市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煤化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会员,燕赵文学签约作家、媒体编辑、记者、鲁迅文学院首届煤矿作家高研班学员;作品在《诗选刊》《诗人周刊》《作家报》《诗导刊》《陕西日报》《当代》《阳光》《河南文学》《陕西文学》《山东诗歌》《安徽诗歌》《陕西诗歌》等发表诗歌、小小说、散文百余篇(首);诗歌作品收录《中国当代诗人诗选》等书中;小说《悲情黄土地之命运篇》收录《在希望的田野上》书中。